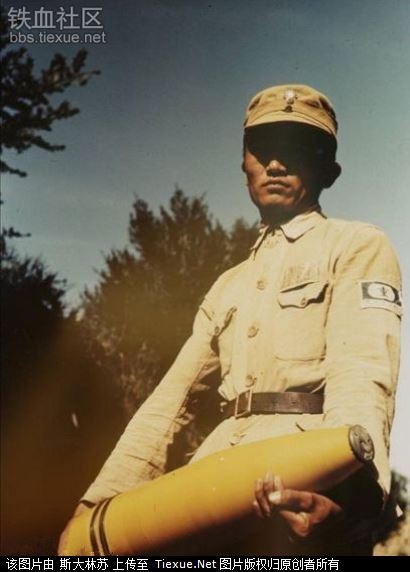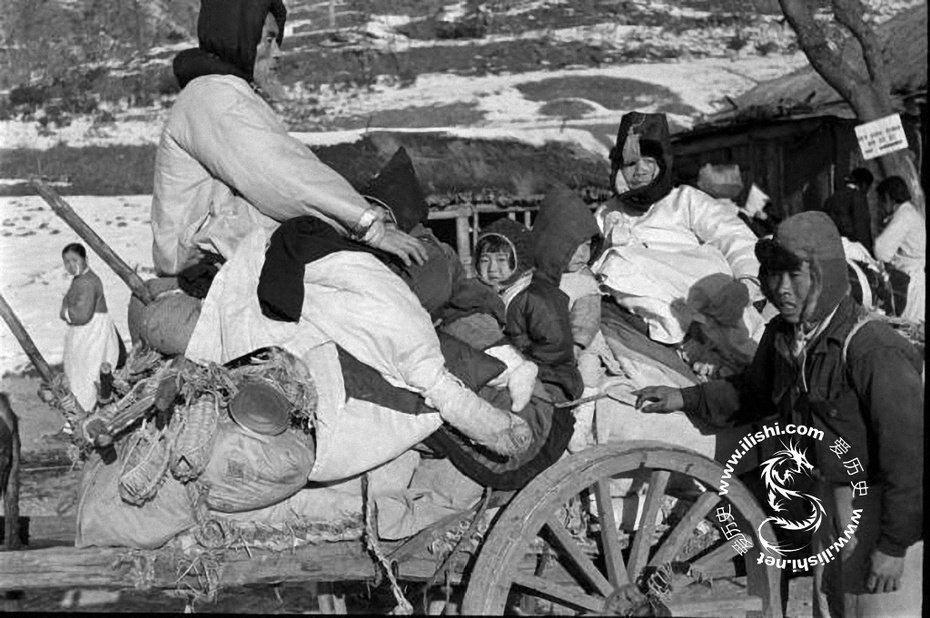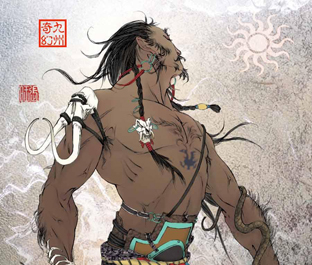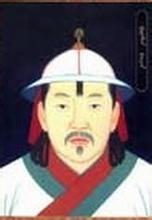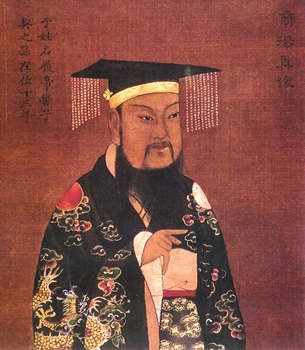作者非兰陵笑笑生?金瓶梅考证疑点多
一种“新说”出现,往往会引起媒体的注意或宣传,有时随手拈来几条材料,作一番遐想式的“新说”也得到同样的礼遇,这就容易诱发出视严肃的学术课题为终南捷径,将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取代科学探讨的危机,助长那种以侥幸求立说的风气。
2003年12月14日,《文汇报》刊登了吴敢先生的《〈金瓶梅〉及其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》。该文题目已肯定了“兰陵笑笑生”的著作权,综述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考证时,虽也言及“标新立异、弄虚作假、东搭西凑、哗众取宠者,时见其例”,但对《金瓶梅》作者考证本身以及其中几种考证却颇为肯定,尽管有“皆无直接证据,都是间接推论”的遗憾,可是“剥茧抽丝、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”等语显为赞誉。然而笔者以为,《金瓶梅》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,“间接推论”已非考证,更何况现在得到的还只是比附与猜测。
一、考证缺乏可靠的前提
要考证一部作品的作者,必须找到距离该作品问世最近的有关说法,并检验其可靠性。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明代人有五种说法:
1、屠本畯《山林经济籍》云:“相传嘉靖时,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,朝廷籍其家。其人沉冤,托之《金瓶梅》。”
2、谢肇浙《金瓶梅跋》云:“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,凭怙奢汰,纵欲无度,而其门客病之,采摭日逐行事,汇以成编,而托之西门庆也。”
3、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云:“旧时京师,有一西门千户,延一绍兴老儒于家。老儒无事,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,以西门庆影其主人,以余影其诸姬。琐碎中有无限烟波,亦非慧人不能。”
4、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云:“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,指斥时事。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,林灵素则指陶仲文,朱&&则指陆炳,其他各有所属云。”
5、《金瓶梅词话》万历四十五年(1617)刻本欣欣子序首句云“窃谓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”,末句又云“笑笑生作此传者,盖有所谓也”;廿公《金瓶梅跋》首句云:“《金瓶梅传》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。”
迄今为止,众多考证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论文中曾征引的各种史料无虑数百,但现知最直接的明代人的说法只有以上五种。它们可明显地分成两类,前四种都是当时名士所言,他们在《金瓶梅》刊行前都接触过甚至誊录过抄本。四种说法互不相同,但从中却可得到三个可以肯定的推断: